米芾(1051-1108),初名黻,字元章,至元佑六年(1091)开始用芾名,自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淮阴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世居太原,迁居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而卒,故《宋史》本传称吴人,徽宗时为书画博士,后任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
米芾学书在传统上下了很大功夫,他虽然仕途困顿,却未卷入政治漩涡,生活相对安定,得以潜心古学,后当上书画博士,饱览内府藏书,熟谙千载故事,古人得失,如数家珍。他少时苦学颜、柳、欧、褚等唐楷,打下了厚实的基本功。苏轼被贬黄州时,他去拜访求教,东坡劝他学晋。元丰五年(1082)开始,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他的书艺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年米芾自称自己的作品是“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都有深刻的领悟,尤其在结字上所作研习最为深透。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绍圣年间,提出了“老厌奴书不玩鹅”的口号,一面学古人,一面骂古人。表明他致力于彻底摆脱古人,寻求自我归宿。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这样说道:“余初学,先学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其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其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摩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泽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宫,《刘宽碑》是也。篆便爱《咀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
米芾的书法在宋四家中,列苏东坡和黄庭坚之后,蔡襄之前。然如果不论苏东坡一代文宗的地位和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的影响,但就书法一门艺术而言,米芾传统功力最为深厚,尤其是行书,实出二者之右。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谓:“吾尝评米字,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于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就现存米芾的作品来看,其书风在中年就已形成,如《研山铭帖》、《致葛君德忱尺牍》、《苕溪诗卷》、《复官帖》、《拜中岳命诗》、《三吴帖》、《乐兄诗》、《寒光二简帖》等,刻石有《方圆庵记》、《诉衷肠帖》、《芜湖县学记》等。此时已形成沉着飞翥、天真绚烂、精力弥满的成熟书风,显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精神。其中《苕溪诗卷》写于1088年,时米芾38岁。《蜀素帖》稍后,侧锋用笔,斜奇欠取势,俊逸爽洁,神采飞扬,为米芾书风代表作品。《拜中岳命诗稿》约为米芾四十二三岁时的作品,行笔外拓,字行宽绰,散朗多姿,融会众长,独具风神,是其风格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墨迹《复官帖》行书90字,字大寸余,此帖为米芾铭心绝品,神韵自然,行笔流美畅达。《多景楼诗册》、《自书天马赋》为米芾晚年早期得意之作,气息畅达,雄健而略显苍劲。《吴江舟中诗卷》是其晚年力作,既有中年书风的痛快淋漓,又有晚年老道的清古从容,枯笔疏行,奇欠侧随意,留下了更多的虚白启人想象。米芾自称自己是“刷字”,这是在面对皇帝的询问下明里自谦而实含自负的回答,“刷”实质上是一种于逆势中放纵跌宕的用笔,从现存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点到精要之处,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无怪乎苏东坡说:“米书超逸入神。”又说“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米芾的书法影响深远,北宋就有蔡卞、曾纡等人受他的影响,到南宋,米友仁克绍家学,高宗学黄山谷后,转学米芾,天下翕然学米。尤在明末,学者甚众,像文徵明、祝允明、陈淳、徐渭、王觉斯、傅山这样的大家也莫不从米子中取一“心经”,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米芾正是以其高妙绝伦的书艺,与苏、黄、蔡一起为宋代赢得了“尚意书风”之赞誉。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其中振聋发聩警策之语不少,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米芾之前,论书者都以王羲之为书圣,其子献之为亚圣。而米芾则认为“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所谓天真,即自然而率真,就是心灵的自然流露,不经意,不矫饰,顺乎自然的书写。裴休书“率意写碑,乃有真趣。”论沈传师书“自有超世真趣。”论颜真卿《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馨露,在于此书。”论杨凝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座位帖》。”在《海岳名言》中,米芾一再强调:“无刻意做作乃佳”,“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把唐人楷书认为“状若算子”。米芾又提倡平淡的书风:“余入晋魏平淡”“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剔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天真平淡”成为米芾书评的最高标准。米芾这种贬唐的态度似乎有些偏Ji了,对于唐代楷书和草书,其跋颜书:“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宝晋英光集·陟闻梓旧》卷八),颜柳是唐代楷书的代表,庄重严整,一派盛唐气象,足以典范后世,之所以不入米芾法眼,是他以晋人为唯一的品评标准的结果。其对草书的认识也是如此,晋人的风格是最高境界,张旭所创草法是违晋人古法的,只能是下品;怀素是如前所述,因为受时代的压制,达不到晋人平淡天成的境界,唐代其他的草书则更不必论了。这种褒晋贬唐的狭隘认识,使米芾的草书束手束脚,成就平平,他的草书留传至今的也很少。不过这些都不能掩盖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历史上兼善诸体均能名世的确是凤毛麟角,宋四家中,苏、黄、蔡皆能精一体,唯米芾五体俱能,我们又怎能过于苛求他呢?
米芾在书法艺术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是由于其长期孜孜以求古人,集各家之长。而其绘画艺术则更多地来源于他的灵感与天赋,并更能充分地展现他的才情与标新的创造精神。
米芾一生以书家自居,作画不多。宋人邓椿亦云:“公(米芾)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如今其画作已佚失很久。据说,米芾作画是在北宋画坛大家李伯时中风后,即元符三年米芾五十岁之际。其实,史书记载在此之前米芾就已临了大量的古人绘画,有时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绘画上,米芾与其在书法上的主张是一致的,也是褒晋贬唐,其人物画取法东晋顾恺之。尽管李伯时是一位大家,米芾却认为他的画欠神采,尝云:“以李(伯时)常师吴生(吴道子),终不能一笔入吴生”。(《画继》,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8月版。)显示了其恃才傲物的一面。
米芾绘画上的成就主要还是在山水画上。他不喜欢作危峰峻岭的北方山水,却情有独钟地作江南的山山水水。虽然他的画作已经看不到,但我们可以从其子米友仁的传世作品中领略到米氏云山独特的神韵。米氏云山的画法是用大小错落的横点点饰出山的形状,上密下疏,上浓下淡,点与点之间自然随意地留出空隙,笔笔可见,云气以淡墨空勾并渲染,树枝多用浓墨简洁勾出,以大浑点作叶,山脚坡岸以淡墨卧笔横扫,此画法乃米老前无古人的独创。连《宋史》也称“米芾在艺术上独具慧眼,有着超凡的感悟力。”米芾在山水画上之所以能自出机枢,一方面得力于其丰富的收藏,因而眼界甚高,下笔不凡;另一方面,其酷爱自然,深入生活,仔细观察,寄情山水。《洞天清录》记云:“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明水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模仿之,遂得天趣。”米芾山水画之中“山水”,影响最大的是镇江的山山水水。其中年定居镇江,海岳庵就在北固山甘露寺下,北固山陡入江中,三面临水,金山、焦山遥相互映,向南远眺,则“云气涨漫,冈岭出没,林树隐现”,俨然一幅天然图画,故而产生了米老画笔下的《海岳庵图》和《金山图》,描绘出了动人的图画,也体现了米老的绘画功力和对镇江山水的热爱之情。
米芾的山水画另辟蹊径,不是正宗传脉,孤清人王世贞谓之“不过一端之学,半日之功耳”,但“米氏云山”确是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语言方式,在山水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董其昌《容台别集》云:“唐人绘画,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诗至少陵,书至鲁公,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董其昌对米芾这样推崇有佳,其著名的“南北宗论”也是以米芾为中心建立起来的。而事实上,米芾提出的“寄兴游心”和“墨戏”的绘画美学思想,崇尚天真平淡的画风,对宋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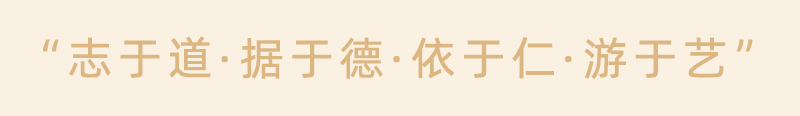
闂佺ǹ绻愮粔鐑芥儗濡や胶鐝堕柣妤€鐗婇~鏍煥濞戣櫕瀚�
闂佸疇顔愰幏锟� 闂佸搫鐗滈崜鐔煎Υ婢跺鈹嶉柍鈺佸暕缁辨牠鏌℃径鍫濆姤闁搞倖绮庣槐鏃堝箣閻樺灚宕熼梺杞扮椤曨參骞冩繝鍥ㄦ櫖閻忕偠妫勫鎾绘煛閸屾碍鎼愰柣鈯欏洤违濞达絽鎲$粋鍫ユ煟濡も偓濞层倝骞忔导瀛橆棅閻庡湱濯ḿ鎺懳涢悧鍫濈仼婵炲牊鍨块獮宥夊焵椤掑倷娌柣鎰摠缂嶁偓閻熸粎澧楃敮鎺旀暜椤愶絾濯存繝濠傛閸嬫捇宕ㄩ纰辨殹闂佸搫鐗嗛ˇ顓㈠焵椤掆偓閸婄懓锕㈤悧鍫涗簻闁稿繐鎽滈惌宀勬煕鐎n偆顣查柡鍡欏枔閳ь剚绋掗〃鍛村船鐎电硶鍋撶涵鍜佹綈缂佷礁顕幏鐘诲即椤忓棛顦Δ鐘靛仦濠€鍦箔婢舵劕绠涢煫鍥ㄦ尰閸ゅ嫰鎮硅閸嬫盯骞冮幘璇茬闁诡垶鍋婂ḿ搴ㄦ煟閹邦垼娼愰柛銊e妿閹风姵鎷呴崫銉︽緰闂佺ǹ绻楀▔娑㈠船鐎电硶鍋撻悷鐗堣础婵炲牊鍨块幆鍥偄妞嬪孩婢栭梺璇″劯娴f彃浜鹃柛灞剧〒閵堟挳鎮归崶銊︾闁哄棛鍠栭獮鎴︻敊閼姐倗鐓傛繛鎾寸缁嬫垿宕幘顔界劸閽橆摨闁诲孩鍐荤紓姘卞姬閸曨剛鈻曢悗锝庡墯閺嗗繘鏌ㄥ☉妯侯殭缂佹顦遍埀顒傛暩閹虫捇藝婵犳艾绠甸柟閭︿簽鏉╂棃鏌℃担鍝勵暭鐎规挷绶氶獮鎺楀Ψ閵夈儳绋夐梺闈涙4閹凤拷
闂佸疇顔愰幏锟� 闂佸搫鐗滈崜鐔煎Υ婢跺⊕鍦偓锝庡幘濡叉悂鏌i妸銉ヮ仼闁哥偛顕埀顒€婀遍幊鎾汇€呰閳藉寰勬繝鍌涘皨闂佸憡甯楁竟鍡樻櫠濡ゅ懎绾ч柛鎰典簽閹煎ジ姊婚崒銈呮珝妞わ絼绮欓弫宥呯暆閸愭儳娈查梺鍛婄懄閸ㄥ潡宕戦弽銊ь浄闁诡垱婢樺▓楣冩煥濞戞瑯鍔杝yx@qq.com 闂佽壈椴稿濠氭焾鐎涙ê绶為柛鏇ㄥ幗閸婏拷



.jpg)
.jpg)
.jpg)

.jpg)
.jpg)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