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艺术的现代以降:梵高、马蒂斯和毕加索以其破坏力十足的艺术风格向传统欧洲艺术发起挑战——此后一个世纪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无不是极富革命性的。
上世纪60年代,“概念艺术”大行其道。从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充满戏谑意味的作品到小野洋子标志性的“事件剧”(happenings)。此类艺术的荣光在某些程度上与波普艺术和时尚艺术进行了价值共享。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一群新兴的英国艺术家——包括戴米恩·赫斯特、翠西·艾敏(Tracey Emin)、杰克·查普曼、迪诺斯·查普曼(Jake and Dinos Chapman)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围绕着性、时尚、艺术和金钱展开创作,他们的作品通常是极富讽刺意味的。然而当他们的作品越来越为人所赏识,售价节节攀升的时候,作品中原有的那层玩世不恭却消失殆尽了。

由英国艺术家翠西·艾敏(Tracey Emin)创作的“概念艺术”作品《床》。
如今的英国亟需发起新一轮的前卫艺术运动,从而让前卫艺术超脱于惯常使用的那些视觉震撼技巧,格雷格尔·缪尔(Gregor Muir)说。缪尔是著名的伦敦当代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的主管,此前曾鼎力支持青年英国艺术家运动。目前,他正竭尽所能为不知名艺术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能够让他们远离被富豪和名人所豢养着的艺术市场,从而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年艺术亚文化。
“如果我们正在寻找某些激进的东西,那么它并不总是意味着要让人们感到震惊。它更多关涉到如何能更加具有穿透力,它关涉到如何能够深入人的内心,”缪尔说,“寻找一个真正的亚文化远比呼吁发起新一轮的‘前卫艺术运动’要重要得多。我们需要听到那些在别的地方从未被代表的文化的声音。”
5年前,缪尔正式掌舵伦敦当代艺术学院,当时学院正濒于经济破产的边缘。本月,当代艺术学院即将迎来70年庆典,缪尔构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用以支持那些在商业艺术市场中一文不名的新生代艺术家。他相信,艺术创作应该远离**经销商和巨富艺术品收藏家的侵扰,唯此,创意灵感才能自在地落地开花。
“这样的创作空间并不位于一个成功的画廊内,也同样不位于一个博物馆中。一个艺术家可以在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中专注地进行艺术创作。这个学院由艺术家和爱好者创立,它是艺术家的栖所,它是艺术的摇篮,”缪尔说,“我们存在的理由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失却了这样一个中间地带,艺术世界将复何及?对于那些至今一文不名、毫无商业价值且又没有明显的市场前景的艺术家来说,又将造成多大的损失?”
在执掌当代艺术学院之前,缪尔曾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和独立画廊豪瑟和沃斯(Hauser and Wirth)工作。2009年,他的《幸运艺术》(Lucky Kunst)一书正式出版,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他和青年英国艺术家运动中涌现的艺术明星之间的趣闻,这本书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本月,当代艺术学院获得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England)提供的187495英镑拨款,并将斥资120万英镑修缮“纳什之家”。位于林荫路上的“纳什之家”是当代艺术学院的驻地。
缪尔表示,伦敦的艺术环境从未像现在这般不利于艺术家成长发展:”一个商业画廊有其规划和盈利的需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商业画廊的规模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也开始模仿博物馆的做法,而不是探索艺术的先锋实验性。”
他的话也回应了安德雷娅·菲利普斯(Andrea Phillips)的担忧。菲利普斯曾是伦敦金史密斯学院的讲师,目前她供职于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在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她表示这一代艺术专业学生“没有一点未来”。艺术市场上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只能“不断讨好有钱的富豪以获得资金支持”。
“青年艺术家透过双年展、艺术博览会和博物馆晚宴清楚地看到了艺术世界的不平等(他们都不会收到邀请)。他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的地位被艺术主流价值所褫夺,”她说。
当代艺术学院共同创立人罗南德·潘罗思(Roland Penrose)爵士曾说过学院的作用在于“刺激艺术家创作,助力那些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奇思妙想”。尽管如此,学院在2002年经历了一段艰难时光,评论圈认为学院正在堕落,饱受争议的主席伊万·马索夫(Ivan Massow)也大言不惭地认为现代艺术都是“自命不凡、随性为之、毫无创意的拼贴,我从不认为把它们视作是上帝的馈赠”,此后,马索夫也正式被解雇。

第56届威尼斯世界艺术双年展览(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上,萨拉·卢卡斯的作品。
2010年,艺术委员会为当代艺术学院下拨了紧急救援基金,并下达了**的最后通牒。当代艺术学院的主管艾可·厄舜(Ekow Eshun)和主席阿兰·耶恩托普(Alan Yentob)相继辞职。艺术经销商、作家卡斯滕·舒伯特(Karsten Schubert)认为当代艺术学院已经被伦敦的其他竞争者甩在身后:“当代艺术学院的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它真的是孕育前卫艺术的唯一场所。如果现在当代艺术学院失去了这个头衔的话,那么原因就在于前卫已经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概念了。”
为了给当代艺术学院创造一个稳健的未来,缪尔希望能够保持学院俱乐部式的创作氛围并重建“纳什之家”。今年在学院举行的展览包括朋克珠宝匠朱迪·布雷莫(Judy Blame)首次个展以及朋克乐队Public Image Limited的专辑设计展。当代艺术学院的电影计划和现场表演也仍将继续。
“要保持学院的品格并不容易——世事也难免有起起落落,”缪尔表示他将继续致力于探讨前卫艺术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主要艺术场所像当代艺术学院这样将重心放在主流视野之外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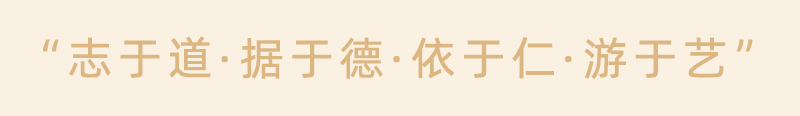
鍏嶈矗澹版槑锛�
鈶� 鏈〉淇℃伅鏉ヨ嚜缃戠粶鏁寸悊锛屽叾鏂囧瓧銆佸浘鐗囧拰闊宠棰戠殑鎵€灞炴潈褰掑師浣滆€呮墍鏈夈€傛湰椤典粎鍋氭暟瀛楀唴瀹规祴璇曪紝骞朵笉鎰忓懗璧炲悓鍏惰鐐规垨璇佸疄鍏跺唴瀹圭殑鐪熷疄鎬с€傛祴璇曟暟鎹粎渚涘唴閮ˋi瀛︿範涔嬬敤锛屼笉瀵瑰鎻愪緵鏁版嵁鎺ュ彛銆�
鈶� 鏈〉娴嬭瘯鐨勫唴瀹瑰娑夊強鍒扮増鏉冪瓑闂锛岃鍙戦偖浠惰嚦锛歴syx@qq.com 鑱旂郴澶勭悊
.jpg)
.jpg)

.jpg)
.jpg)
.jpg)

.jpg)